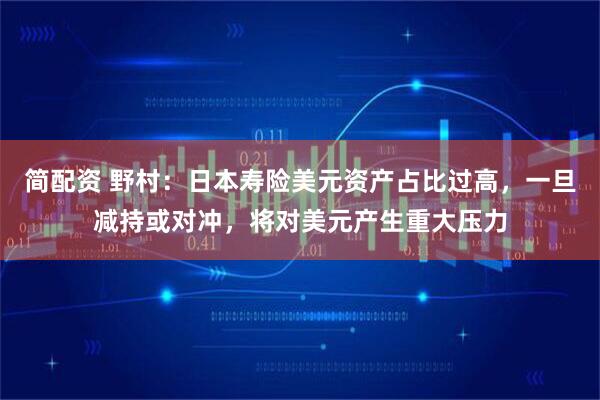1951年2月4日宏图优配,朝鲜前线。寒风裹挟着碎雪呼啸掠过山谷,黑暗中吕奇良压低声音问:“参谋长,美军真的会相信我说的话吗?”当时没有人能给他答案。数日之后,他才明白,美军确实信了,可结果却与他幻想中的完全不同。
吕奇良原本是26军77师264团三连的一名干部。长津湖战役后,26军因行军受阻背上了“耽误战机”的黑锅。军部下令调整,262团被降格为特务团,264团编入77师。番号的削减就像一根冰冷的尖针,深深扎进每一名官兵心口。没人愿提,但谁也无法忘记。这种压抑氛围下,吕奇良选择了最极端的“出路”——叛逃。按志愿军编制来看,他是迄今叛变级别最高的干部。
消息传到大邱的美军司令李奇微耳中,他立刻振奋。原因很简单:吕奇良来自宋时轮指挥的第九兵团,而长津湖一役让美军对该兵团心有余悸。李奇微专门派飞机将吕奇良从前线接走,亲自接待,甚至殷勤奉茶,称其为“座上宾”。随后,美军法庭、反情报人员与翻译官接连登场,逼问的核心只有一个:第九兵团的战力如何?
展开剩余79%吕奇良的回答是:“88师已撤销,26军弹药匮乏,已无力再战。”此言一出,美军作战处军官们喜形于色。李奇微甚至对副官感慨:“或许我们把中国人想得太神了。”于是,一份针对26军的穿插作战计划迅速出炉,执行任务的美25师24团自信满满,认为只需一次突击,便能撕开志愿军防线。
可战场从不按照设想展开。2月下旬宏图优配,汉滩川畔骤降至零下二十度,河面冰层轰鸣作响。美军24团一个营摸黑泅渡,测绘员草率判断水深“不足一米”,可河心竟有一米五。士兵们刚入水,急流便卷走数人,惊叫声划破夜空。潜伏在岸边的志愿军262团瞬间开火,密集的机枪弹把冰冷水面搅成沸腾,一轮交火不到十分钟,美军伤亡过半。
然而25师师部仍自欺为“疏漏”,命令继续强攻。无论多少兵力推上去,都被对岸层层交织的火网击退。子弹打尽,炮火哑声,士兵们哭喊着后退。布拉德利师长怒不可遏,强令团长布里斯特“必须拂晓前攻下山头”。布里斯特却吞吞吐吐地回答:“我们的兵……在重组。”事实是,所谓的“重组”已退至十几公里外的土耳其旅营地。那里,大批湿透的美军士兵围着火盆取暖,死活不愿回到战场。
志愿军262团并未死战。团长张仁初冷静下令:“拖够时间即可,别死扛。”天色微明,他们有序撤离。美军终于摇摇晃晃占上山头。李奇微通过航拍得知阵地“已夺取”,心里稍安,但当夜的伤亡数字摆上桌面时,他的脸色瞬间铁青——24团一夜伤亡六百余人,却几乎毫无战果。此事在联合国军会议上引发耻笑,李奇微不得不当场下令撤销第25师24团番号。
种子山战役的结果,是志愿军仅用一个加强团,便让美军付出惨重代价。随后的第五次战役,美军再也不敢轻视26军。军报统计,1951年夏季,26军作战共歼敌五千六百余人,俘虏七百余,缴获火炮数量刷新纪录。被降格的262团更因战功赫赫荣立集体一等功,全军通报表彰。“排炮打不动的老八纵”称号再次被官兵们自豪地挂在嘴边。
而吕奇良呢?当美军“礼送”他回到战场交换点时,他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被利用的一枚弃子。很快,军事法庭判处他死缓并撤销军籍。判决文件下达26军后,无一人为他开口求情。有人冷笑:“一个连队能掉队,一个人更容易掉队。”更讽刺的是,他口中所谓“枯竭”的部队,却用血肉之躯击退了世界最强陆军,反手让美军栽下建军史上的大笑柄。
追溯26军番号前身,更能理解他们为何总能“翻篇”。解放战争时期,八纵自弋阳杀到上海,九昼夜鏖战歼敌四万;淮海战役,22师64团七人竟迫使一千五百人的敌团长率部投降;七峰山,更是262团九人班半小时炸毁美军十一辆坦克。此类战例被写入教材,被称为“神仙操作”。这种底蕴,不是一场挫折就能抹去的。
韩战后期,“冷枪冷炮运动”风靡全线,26军多项战法成为源头。统计显示,运动期间,26军击毙敌军三万八千余人,五十多名狙击手个人战绩破百。实践证明,哪怕敌人装备再先进,只要与老八纵近身,他们就必须掂量后果。
再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——“美军真会信我说的话吗?”答案是:他们信了,但付出的却是尴尬数字、撤销番号和难以抹去的耻辱。对一支血战多年的队伍而言,一个叛徒掀不起风浪;而对依赖情报与技术的美军来说,一次轻敌却足以酿成惨痛代价。历史给出的评语冷峻而清晰:轻视中国军队,都是危险的奢侈。
七十余年过去,朝鲜半岛已无硝烟,262团战士的名字渐渐淡出报纸和口号。但那一夜种子山的短促火力点射,仍是军事课堂的经典案例。有人分析数据,有人拆解战术,而更令人动容的,是那句质朴总结:“知耻而后勇,才是真勇。”这句话,不仅属于26军,也属于那个硝烟弥漫的新中国黎明。
发布于:天津市乐盈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